- 相關推薦
《滄浪詩話》詩詞鑒賞
《滄浪詩話》是南宋詩論家嚴羽創作的詩歌理論著作,大約在紹定(1228—1233)前、至遲在淳祐(1241—1252)前成書。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滄浪詩話》詩詞鑒賞,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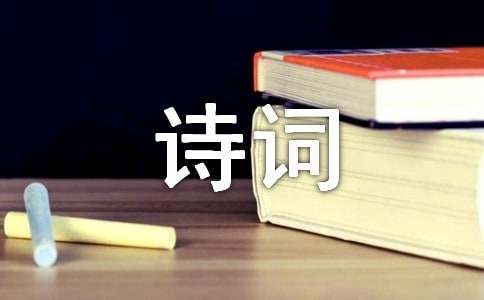
《滄浪詩話》詩詞鑒賞
“少陵詩法如孫吳, 太白詩法如李廣。少陵如節制之師。”所謂節制之師, 是說老杜詩歌嚴整且有法度可循。陳俊卿《石溪詩話序》也說:“杜子美詩人冠冕, 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嚴, 而流落困躓之中, 未嘗一日忘朝廷也。”句法森嚴也是就這一點來說的。而據《史記李將軍列傳》載, 李廣將兵無部伍行陣, 治兵極為簡易靈活。無部伍行陣是與節制之師相對而言的。嚴羽說太白詩法如李廣, 很顯然是指其詩法無一定規則、變化多端。如嚴羽評《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巧如蠶, 活如龍, 回身作繭, 噓氣成云, 不由造得。是歌須看其主、伴變幻。題立‘峨眉'作主, 而以‘巴東'、‘三峽'、‘滄海'、‘黃鶴樓'、‘長安陌'與‘秦川'、‘吳越'伴之, 帝都又是主中主;題用‘月'作主, 而以‘風'、‘云'作伴, ‘我'與‘君'又是主中主。回環散見, 映帶生輝, 真有月印千江之妙, 非擬議所能學。”是指其詩法的變化。
(一) 下字之法
《滄浪詩話詩評》云:“下字貴響, 造語貴圓。”指出作詩下字應有力度。如評李白《山人勸酒》詩云:“‘歘起'二字有大海回瀾之力。”評《獻從叔當涂宰陽冰》云:“‘精'、‘氣'字佳, ‘精'字更難下。‘激昂'與‘協'字俱有力, 有身分。”此等力量, 他人絕難企及。再如, 評《白紵辭》:“‘歌吹'著‘濛'字, 不獨曛色迴翔, 亦覺音響潤澤。”評《月夜聽盧子順彈琴》云:“一毫不做, 而‘夜'字安, 頓覺異。”此為一字之法。評《秋日煉藥院鑷白發贈元六兄林宗》云:“以‘豈'、‘初'二虛字見卷舒。”則為下虛字之法。
在下字之法上, 《滄浪詩話詩評》又提出:“《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郁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 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 纖纖出素手。'一連六句, 皆用疊字, 今人必以為句法重復之甚。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頗為關注疊字的運用, 并指出宋人以連用疊字為句法繁復的觀念是錯誤的, 因《古詩十九首》正有此法。事實上, 這種連用疊字之法并不首見于《古詩十九首》, 而始于《詩經衛風碩人》:“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施罛穢穢, 鳣鮪發發, 葭菼揭揭, 庶姜孽孽。”李白詩歌中也多有連用疊字的現象。如, 《秋浦歌》中“千千石楠樹, 萬萬女貞林。山山白鷺滿, 澗澗白猿吟”。對此, 嚴羽評:“‘山山'、‘澗澗'可學, ‘千千'、‘萬萬'不可學。”評《飛龍引》:“多疊語, 如兒謠。”再如, 《上三峽》:“三朝上黃牛, 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 不覺鬢成絲。”以三朝、三暮做疊, 殊為別致, 造成聲情無盡的效果。嚴羽評之:“從謠音再疊, 情似《陽關》。”
(二) 句法、章法
關于詩歌中的句法, 《滄浪詩話詩法》云:“對句好可得, 結句好難得, 發句好尤難得。”由此可見, 嚴羽特別注意李白詩歌的起句及結句之法。如, 他評《古朗月行》:“起手點趣。”評《擬古十二首涉江弄秋水》:“只須起四句, 成古樂府。”評《對酒憶賀監二首狂客歸四明》:“起句只一顛倒, 有風雅之格。”評《勞勞亭》:“起句一口吸盡。”評《月下獨酌四首天若不愛酒》:“起四句極豪率, 卻極雅蘊。”評《鸚鵡洲懷禰衡》:“起二句好眼孔、好識力, 能不遂常見。”均著眼于起句。而關于詩中句法, 嚴羽評《白頭吟》:“東流、落花句與上寧同、不忍句相呼應。歡則愿死聚, 怨則愿生離, 皆鐘情語。”指出, “東流不作西歸水, 落花辭條羞故林”句與“寧同萬死碎綺翼, 不忍云間兩分張”句相互呼應。評《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劍閣重關蜀北門》:“以中一句對上二句, 以下一句收三句, 是一法。”評《臨江王節士歌》:“本《騷》‘洞庭始波木葉下'來, 一變為此, 再變為‘洞庭始波木葉微'說, 增趣轉多, 初味欲散, 醍醐酥酪當細辨之。”在詩歌創作中, 起句與結句最難, 而結句要以不著跡為佳, 明謝榛《四溟詩話》云:“結句當如撞鐘, 清音有馀。”即為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意。嚴羽評李白《蜀道難》:“一結言盡意無盡。”《鞠歌行》:“結末謂舉世不足與目遇也, 寄慨超遠。”《梁甫吟》:“看結句更知用意之妙。”《游謝氏山亭》:“起語情甚別。末四句亦堪作絕。”
李白詩歌章法亦多變化。嚴羽評李白《口號贈徵君鴻》:“將頭作尾, 亦復無首無尾。此格甚異, 若以為犯, 必非知詩者。”此詩以陶淵明、梁鴻起;以楊伯起做結, 卻都旨在贊美隱逸高士的情懷, 因此嚴羽評其無首無尾。再如, 《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此格如常山蛇, 首尾與中皆相應。”陳善《捫虱新話》解釋了何為常山蛇勢:“桓溫見《八陣圖》曰:‘此常山蛇勢也。擊其首則尾應, 擊其尾則首應, 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予謂此非特兵法, 亦文章法也。文章亦要宛轉回復, 首尾俱應, 乃為盡善。”于此, 李白詩歌章法之妙可窺一斑。他評《五松山送殷淑》:“篇章秀特, 不作順流而下。於己法中亦稍異。”評《贈汪倫》:“才子神童出口成詩者多如此, 前夷后勁。”等文句, 也可窺見李白詩歌章法確實如李廣將兵, 不循成例而多變化。
(三) 使事
宋人以才學為詩的表現之一是在詩歌中大量用典, 并標榜以“無一字無來處”。嚴羽批評了這種極端現象。《滄浪詩話校釋詩辯》指出, “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 遂以文字為詩, 以才學為詩, 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 終非古人之詩也, 蓋於一唱三嘆之音, 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 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 押韻必有出處, 讀之反覆終篇, 不知著到何在。”《滄浪詩話校釋詩法》又提出:“押韻不必有出處, 用字不必拘來歷。”“不必拘來歷”是嚴羽所提倡的, 他在評點李白詩歌時反復論證了這一觀點。如, 評《胡無人》詩“天兵照雪下玉關, 虜箭如沙射金甲”句:“若言‘雪照天兵'便尋常, 正不必引釋出處, 一有來歷反無味矣。”“雪照天兵”為常格, 而李白偏說“天兵照雪”, 使其詩句別具一種英爽之氣, 因此, 嚴羽認為大可不必引釋其出處, 因為一有來歷反覺無味, 洵為知言。此外, 評《古風大雅久不作》中:“‘秋旻'有眼, 若讀《爾雅》太熟, 但認作有來歷, 非知詩者矣。”評《春日行》云:“‘弦將手語'四字無所本, 不嫌造, 此, 真天才。”評《鳳臺曲》詩“人吹彩簫去, 天借綠云迎”句:“‘借'字不必有來歷, 然不覺其尖鑿, 所以為佳。”
但是, 嚴羽并不反對詩歌中的精準用事, 以及能與作者情性相應的典故。如, 《古風抱玉入楚國》詩:“抱玉入楚國, 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 徒勞三獻君。”此詩用卞和向楚君獻璧而良寶見棄之事抒發忠臣遭謗和懷才不遇的感憤, 用事與詩旨泯然相契。因而, 嚴羽評此詩時, 云:“用事如此, 方有論、有情、有識。”再如, 他評《擬古月色不可掃》:“一結用費長房事, 乃入渾冥。”評《贈裴司馬》“用裴書則事, 如此醞藉。”等, 都是李白詩歌用典之善者。
后世影響
《滄浪詩話》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是一部以總結前人論說見長,而又使之系統化的著作。它出現于南宋后期那樣一個特殊的年代,有其糾正詩壇以學問為詩偏弊的正面效用。它鮮明地提出了詩歌藝術的美學特點和審美意識活動的特殊規律性問題,觸及藝術形象和形象思維的某些重要的方面,把傳統的美學理論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它系統地論述了詩歌體裁的類別和詩歌風格的流變,不僅有助于養成良好的詩“識”,也反映出某種程度的文學進化觀念;而關于唐詩分期的研究和對盛唐詩風的標榜,更成為建立唐詩學的濫觴。
《滄浪詩話》在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文壇影響頗大。近人陳衍等編纂的《福建通志》談到:“自羽以妙遠言詩……邑人上官偉長、吳夢易、朱叔大、黃裳、吳陵盛傳宗派,幾與黃魯直江西詩派并行。”元代楊士弘選編《唐音》,推尊盛唐,定立“始音”“正音”“遺響”等名目,當也受到《滄浪詩話》的直接啟示。明清詩學中,不僅“格調”“性靈”“神韻”諸派詩論都將此書作為立論的根據,就是一些獨樹一幟的理論家如王夫之、葉燮、王國維等,也都借鑒了《滄浪詩話》的理論思維經驗,推陳出新。明代前后七子講求“格調”,推崇盛唐詩歌的文學主張,即可追溯到此書。清代王士禛繼嚴羽“妙悟”說之后,復提出“神韻”說,又將嚴羽偏愛而又未過于強調的唐詩恬淡空靈一路風格推崇到極致。其后袁枚倡“性靈”說,雖取徑與嚴羽不盡相同,立論則與此書不無關聯。另外,從高棅《唐詩品匯》直到沈德潛《唐詩別裁》,歷來的唐詩選本和唐詩學研究中,也都可以看出《滄浪詩話》的影響。
《滄浪詩話》對后世的影響也有消極的一面。明清詩論和詩歌創作中重藝術輕思想的傾向,亦步亦趨摹擬古人格律、聲調的習氣,靳靳然分唐界宋和別白“初、盛、中、晚”、泥而不化的偏失,也都由《滄浪詩話》肇其端始。鑒于此書自明代以來在士子中甚為流行,錢謙益等明末及清代學者又攻之不遺余力,以致出現了專門批駁此書的《嚴氏糾謬》。
創作背景
宋詩早期較多因襲唐人,中間變革唐風,晚期則又趨近唐調。大致說來,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詩歌創作,都還沒有擺脫對唐人的直接模仿。其間以白居易為效法對象的,有徐鉉、李昉、王禹偁等;以賈島為效法對象的,有寇準、魏野和九僧等;以李商隱為效法對象的,有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他們詩歌創作的成就不一,但都沒有超越唐人的范圍,缺乏創新。仁宗天圣(1023—1032)以后,詩壇上崛起了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一批新人。他們不滿于當時流行詩體專尚文辭雕琢而氣格萎靡,在接受韓愈、孟郊一派散文化詩風影響的基礎上,開創了宋詩的新風貌。到神宗、哲宗時,更有王安石、蘇軾、黃庭堅三位詩人出來,與唐詩面貌迥然不同的新詩風至此形成。王安石的文學才能為政治業績所掩,詩歌的影響也不及蘇、黃二人。蘇軾的詩歌重才氣,任天分,筆意放縱而不加檢束,成就雖高,后人卻難以追摹;黃庭堅的詩歌則尚法度,用人工,字鍛句煉以形成一家的格律,便于人們效法、趨從。所以雖然時人以“蘇黃”并稱,但是后來宗奉黃庭堅的人超過了蘇軾,以致形成了一個很有影響的詩歌流派——“江西詩派”,由北宋后期一直延續到南宋末年,成為傳統所謂宋詩的正宗。
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詩主流,突破了唐以前詩歌“吟詠情性”的傳統,把許多原來不入詩的材料都寫入詩中,寫法上又往往采用散文化的敘述手法和結構形式,從而形成了拗峭生硬的格調。宋詩的變革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它擴大了詩歌的題材和意境,豐富了詩歌的表現手法,從多方面錘煉了詩歌的語言形式。但刻意走散文化的道路,也給宋詩帶來了一系列的弊病。宋人詩中好發議論,原本未必不佳,但總體來看,宋詩的議論化卻用過了頭。詩人們往往熱衷于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的見解,以通篇的說理取代詩情畫意的表現,導致詩歌寡情乏味。喜歡在詩中賣弄才學,搬用典故,是宋詩的又一種風氣。宋人用典常有自出新意的表現,但用得過多過濫,造成文字堆砌和詩意艱澀的弊病,則是普遍的情形。宋人詩歌寫作中還有片面注重煉字琢句的傾向。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人在這方面的弊病都還不嚴重,王安石始有此種傾向,至黃庭堅及江西派諸詩人,就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黃庭堅很講究句法,常把語句烹煉得省凈無余,盡量緊縮句子成分,刪除不必要的虛詞;又喜歡改變語法結構,顛倒詞序,取得句意曲折、文氣跌宕的效果。這些缺點還影響到了整個江西詩派。
以蘇、黃為代表的詩風,既然有許多弊病,不免引起人們的不滿。北宋后期,已有人對他們提出責難,但只是一枝一節的評論。南宋以后,經過靖康之變的刺激,有識之士開始用詩歌來揭示國家的危機,抒寫內心憤懣,于是愈加感到詩中發空論、琢弄文字的可厭。對于蘇、黃詩風的全面攻擊,就由張戒的《歲寒堂詩話》首發其端,此后對蘇、黃詩風的批評便多了起來,顯示了反傳統的共同趨勢。與此同時,詩人們在創作上也開始探索新的途徑。南宋初年的江西派詩人呂本中,為了補救當時詩作拘守法度、門徑狹窄的弊病,提出了“活法”的口號。稍后,號稱“南宋四大家”的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登上了詩壇。他們雖然創作成就很高,卻沒有明確標舉不同于江西派的學詩宗主,也就未能形成和江西派相對抗的詩歌流派。到南宋中葉,有稱作“永嘉四靈”的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四位詩人出來,提倡學習以賈島、姚合為代表的晚唐詩。他們的作品一反宋詩傳統,不發議論,少用典故,也不崇尚文字的奇峭,專用白描手法寫眼前景、心頭事,又特別注重語言的精瑩和對仗的工整,力求傳達出一種靈秀清潤的風味。這對讀膩了江西詩的人來說,必然會引起新鮮的感受。再加上當時學者葉適為之鼓吹,于是一時紛紛效從,蔚然成風,形成晚唐派與江西派互相抗衡和代興的局面。
但是,“四靈”的詩歌雖然在辭句的琢煉上有一定功力,而內容貧乏、氣局狹小卻是其致命傷。他們缺少充實的生活和豐富的情趣,光以鐫寫細物小景為能事,又不愛作古體詩和七言詩,專工五律,甚至全部精力只用在其中的一兩聯警句上。繼起的“江湖派”詩人,盡管所作不限于五律,用筆也比較放暢,而取材多瑣屑,氣格多卑弱,仍與“四靈”一脈相承。“四靈”和“江湖派”既然都存在明顯的缺陷,也就未能給予殘存的江西派勢力以決定性打擊。江西與晚唐之爭,貫串了整個南宋后期的詩壇,嚴羽的《滄浪詩話》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產生的。其撰述目的,在于批駁宋詩發展中的某些不良傾向,尤其是當時盛行的江西詩派的詩歌創作理論與方法,并且為后學作詩評詩提供一個作者自認為正確的門徑。
【《滄浪詩話》詩詞鑒賞】相關文章:
金縷歌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古詩詞鑒賞12-07
經典的詩詞與鑒賞12-09
詩詞鑒賞11-23
詩詞鑒賞05-27
經典詩詞鑒賞精選12-09
經典思鄉詩詞鑒賞12-06
《永遇樂》詩詞鑒賞12-07
詩詞鑒賞教案06-07
(精品)詩詞鑒賞05-28